![]()
决策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
文 / 董事长 陶勇
制造三聚氰胺的张玉军的死刑判决由河北省高级法院维持原判,至此,随着三鹿的破产、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司法审判的终结,似乎三鹿事件的大幕已经逐渐落了下来。但是,去网上搜一搜,却可以发现,这个事件引出的对一个行业的道德质疑,似乎并没有偃旗息鼓。三鹿事件让我们看到了“我们都知道,就是你们不知道”的黑洞,也让我们了解了“虽然在我们手里坏了事,只有坏人才是坏人,我们都不是坏人”竟然还是一种道理。
在三鹿事件中,三鹿之所以被绑上了道德和经济的耻辱柱,法律依据的关键是“明知故犯”,是在“明知三鹿牌婴幼儿系列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情况下,仍准许库存产品三聚氰胺含量 10 毫克 / 公斤以下的出厂销售。”但是,公诉机构的起诉的开始日期是在 8 月 1 日 ,是“在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出具检测报告,确认三鹿集团送检的奶粉样品中含有三聚氰胺”之后。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三鹿以及这个行业对三聚氰胺的“熟视无睹的知”,就不算是“知”了。
关于“知”与“不知”的判断混淆,关键在于这个行业的 “奶户 —— 收奶员 —— 奶站 —— 生产厂” 的结构。奶制品企业从奶站收购鲜奶,但是由于奶户、收奶员和奶站都不隶属于奶制品企业,只是奶制品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供应商,在国家没有规定生产厂检测三聚氰胺的背景下,一个黑洞就产生了。尽管奶站加水、加防腐剂、还加三聚氰胺在这个行业几乎尽人皆知,但由于奶站处于奶制品企业的大墙之外,也处于奶制品企业的“三张财务报表” 构成的经济和法律的高墙之外,奶制品企业虽然经历了巨大的“公共危机”,竟然全部算作“不知”,也就全部免责(除三鹿的“明知故犯”之外)了。
“这是全行业的一个‘脓包',这次很不幸,被我们三鹿给挤破了。”这是三鹿的一位员工在事发后的评论,真是发人深省。这句话提出的问题,直指整个行业,直指这个行业中的企业领导人,问的是决策背后的道德,问的是企业在“三张表”以外的责任。
决策与决策道德
我的导师罗纳德·海沃德( Ronald A. Howard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大学的决策学 权威 教授)前两年出版了一本书 —— 《决策的道德》( Decision Ethics ),书里讨论了决策价值的金三角,也就是决策价值的三个维度,即利益、法律和道德。
决策的结果是行动,是一个行动方案带来的不可逆的资源配置。要判断一个行动是否符合道德,可以从这三个维度展开。在利益的维度中,我们区分的是一个行动是否于我们有利。对于个人,可以是是否现在该买房子了,也可以是是否需要换个工作。对于企业,则可能会是围绕着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我们平衡不同的议题,算计可能的盈亏,权衡各种风险,大都是围绕着这个维度。
在法律的范畴中,我们要判断的是一个行动是否合法。法律规定了我们不能做什么,也规定了如果做了规定不能做的事,会受到什么惩罚,同时还规定我们的责任。对于企业来说,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就是不能做的,做了(又是领导,像三鹿的前董事长)就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但企业按规定交税,就是企业的责任。
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决策中我们往往遇到的是三个维度上的价值冲突。简单的情况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不一定合法,更不一定合乎道德;这在过去三十年中尤其如此,前一阶段讨论的“企业原罪”,就是这个情形。反过来说,符合道德的,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利益,比如:借钱还钱是个基本道德。但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杨白劳比黄世仁还凶”的利益驱动现象。复杂一点的情况是,符合法律的,不一定符合道德,三鹿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制度上的黑洞,当然就属于这一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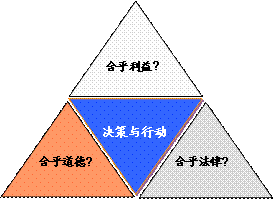
一个决策的行动,有其背后价值的取舍,这也是对决策和行动的一个限制。在讨论价值取舍的时候,这个三角就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如果我们要求企业的决策既合乎利益,又合乎法律,还要合乎道德,那么我们的决策和行动的空间只能是中间的“倒三角形”。但是,如果我们突破了某一个界限,比如:把道德的这个界限突破了,企业行动范围难道不就扩大了很多——去掉了道德这个限制之后,就可以去采取违反道德的行动,决策人就增加了决策和行动的空间,就多了很多方案的选择。同样,如果法律的限制可以突破,一个企业可以做的事也就多了许多。
把法律和利益混为一谈的经典案例之一,应该是安然公司的 CFO 安德鲁·法斯特( Andrew Fastow )。在安然事件爆发出来之前,法斯特在一次对 CFO 杂志的采访中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些创新方法,降低了安然的资本成本。后来人们才发现,他的“创新方法”不过是把债务放到了资产负债表外的资产上。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安然的决策,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安然要扩展,就需要资本;在资本市场获得好评,就需要“亮丽”的财务报表。这些暂时还都是利益的范畴。但是,由于举债发展,安然的财务报表就会不太好看,可能的做法之一就是做些“财务报表创新”,这时候利益、道德和法律就开始了互动。安然的决策是走出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边缘,也许当时还是有些模糊的边界。后来的结果,也就不必细说了。 CFO 安德鲁·法斯特( Andrew Fastow )被判六年徒刑的理由之一,还是欺诈。
这个金三角的理想模型是:道德和法律都是限制,在这两个限制的基础之上,企业可以无限地发挥想象力和执行力,去扩大利益,创造价值。一旦把作为基础的这两个三角形打开,决策和行动的空间自然就延伸开来、扩展开来,就给企业带来更多选择。但是,当这两个作为基础的准绳改变了,就会因为行动的空间扩大,同时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风险——就要冒着违法的风险、违反道德的风险、被人谴责的风险。在今天的社会,法律和道德风险给企业带来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对于违反道德的行动,社会对企业一贯的惩罚都是孤立——因为你不符合道德,大家没人愿意跟你来往,你就变成一个孤立的个体,就没法做生意了。其实,最终你会发现道德是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
在小额金融的实践中,多户联保是一个信用体制的创新。一户借钱,要多户联保,这个人还不了钱了,就要由保人来还。试想一下,在这个制度中,一个人总是不还钱,就是既违反了合约,又违反了道德,长此下去,肯定是没人跟他玩了。一个村子 5 户联保也好, 8 户联保也好,最后总会剩下几个人,没人愿意跟他们联保,他们甚至也不愿意互相联保,也就借不到钱了,这就是违反道德的结果。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村子里每个人的信誉。
总的来说,法律还是比道德清晰的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说的是坏事总会有人管。但是道德不然,总是有些模糊,不同时代还有不同的准则。对这一点, Howard 有个观点,道德就是你在黑暗中面对自己和上帝时的思想。这就是说,道德是一个人在没有任何人监视,或一个企业在没有任何外界和社会监督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所采取的行动。个人和企业一系列的行动的边界,就是他的道德——即便大部分行动没超越道德的界限,没有违反道德的规范,只要有一部分违反了,那就要拿超越界限的行动来说事。决策和行动的边界代表了一个人和一个企业的道德水平,决策和行动跨过了道德的边界,那就是违反了道德。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做一点有道德的事并不难,难的是永远做有道德的事。要看的就是这个边界。
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做的事情是不是道德的。如果你是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一件事,也没有义务告知所有其他的人,那么在边界不很清楚的情况之下,只要想象一下,你要把你的行动向社会公开、向网络公开,特别是与这个行动可能影响的相关利益者讨论——如果你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感到这件事可能不能做,感到不妙,感到难以启齿,就可能有问题了。
三鹿事件表明,企业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会给社会和自身都带来巨大危害。同时,奶制品行业众多企业的“免责”又把我们引向另一个话题:企业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风险
如果我们把三鹿事件放到“金三角”里,就可以看一看当时的市场结构下的奶制品企业的决策。在没有强制性三聚氰胺检测的条件下,奶制品企业在法律上只需要奶站承诺没有加三聚氰胺,就可以说“不知”,就可以免责。这是当时市场结构下的制度缺陷。属于法律范畴。但是,奶站加水,再加三聚氰胺在当时已经是行业广为人知的现象。这时候,奶制品企业可以选择自愿采购检测设备、加强内控,或者是主动调整行业结构,也可以选择利用法律的缺陷,把眼睛闭上,假装“不知”。这是道德的范畴。从结果上看,他们选择了后者。而前两个选择,到了后来都变成了强制性措施。
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场运动,其发端之一就是一系列与三鹿事件类似的事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批美国的消费品品牌成了媒体的关照对象。当时,这些服装、运动鞋等消费品的“大牌”已经逐步把生产基地转到了发展中国家,交给第三方供应商生产。调查发现,这些第三方供应商的工厂里,存在着大量触目惊心的违反劳工权益的做法,包括雇佣童工、超时加班、缺乏基本的劳动保护条件和安全措施,等等。调查结果捅到了媒体上,就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这些国际知名品牌最初的态度与三鹿事件中的奶制品企业的态度一样,“不是我做的,我就不违法;我没有看见,我也就没有违反道德。”但是,公众和消费者则完全不接受这个道理,而这就让这些“大品牌”胆颤心惊了,因为消费者“不买你的这个道理的账”,就会“不买你的品牌的帐”。于是,管理供应商的法律和道德和“合规”,也就逐渐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一个标准项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意味着企业不能再躲在由治理结构、财务报表与合同关系组成的高墙之内,说“外面的事都不是我的责任”了。企业的目的是通过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最大化股东价值。但是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由此产生所有的行动都会对周边的社会和环境产生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界定实现经济价值的过程中,企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划定了这个边界之后,就发现原来的由治理结构、财务报表与合同关系组成的高墙倒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与周边社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与相关利益者的互动,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图画。
回到决策价值的金三角,我们还会发现,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下,这三个三角形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了,企业决策的复杂度和难度都大大提高了,因为企业必须从责任出发,从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互动出发,从道德和法律出发,做出自己的发展决策和行动计划。在这个新的结构中,道德和法律不是利益决策的平衡因素,而是利益决策的出发点。
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代表着企业的道德水平。然而,道德比起法律要复杂许多,法律大部分是说一个企业不能做什么,从对人的资源和能量的要求来说,法律都是被动的,属于“负能量”——你也不用花太多的能量,专门说要做什么事情才能符合法律。道德就不太一样了,道德也有被动的,说一个企业不能做什么,但也有许多是主动的,说的一个企业应该做什么,最好是做什么。做主动的事,比如慈善捐款,就要付出,要投入资源,也要付出努力,是正向的能量投入。因此对于企业来说,社会责任的承担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避免不能做的,一方面是全面考察、审慎决策要做哪些应该做的。
与三鹿事件的奶制品企业的所作所为相对应的是行业垄断企业的创新。垄断企业规避创新是经济学教科书的经典分析,在许多行业的发展中也有许多案例,比如:美国的汽车行业和移动通信行业。创新对于集中度低、竞争激烈的行业是未来生存的必由之路,但对于处于行业垄断的企业,特别是处于行业垄断企业的大型国企,则是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试想,如果处于行业垄断地位的企业不去创新,这个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就会长久地处于低水平,这个行业在全球的竞争地位就难以提高。这时候,企业对创新的投入,就不能只从股东的当期利益考虑,更要从国家、行业、客户、产业链等多个相关利益者的角度考虑。如果这样的企业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谋划创新、鼓励创新、开展创新,反过来又可以为股东带来更为可持续的投资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也许可以分三大类,或者说企业社会责任的所有的行为都可以从这三类别进行分析。第一类,是为所有相关利益者都带来好处的行为,这是要大力推动的方向;第二类是对部分相关利益者有益,但不一定对所有相关利益者有益的行为,这是要审慎决策的行动;第三类,是不应该的行为,我们前面谈过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敢不敢向广大的社会公众公开这个行为。这是要规避和避免的领域。
今天,随着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日益提高,企业在社会责任管理上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了。对于社会责任风险的防范,主要指的就是后两类行动,特别是第三类行动。一般的风险定义,是指某一个行动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或者低于预期的,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定义,不仅包括负向的损失,还包括机会成本的损失。如果企业行动的结果低于利益相关者的预期,就会给企业带来企业社会责任风险。从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的角度看,企业一定要改变自己看自己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企业自己对自己行为的预期,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互动的行动中,社会对企业的预期。比如,在整个三鹿事件全过程中(包括,三鹿事件“发作”之前,奶制品企业“失语”),奶制品企业的表现是低于社会预期的。在这个事件中,企业社会责任的“不作为”,带来的是社会的损失,也是企业的损失,如果要计算机会成本的话,一个行业的企业是很难承受得起的。
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我认为最合适的一个形容词,是高尚,说这个人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形容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做得是好是坏,是不是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企业,如果社会对其评价是高尚,就说明它尽到了企业社会责任。三鹿事件的反面教训,说到底就是两句话,道德是一个企业最长远的利益;企业社会责任,代表着一个企业的道德水准。在全球范围内能用高尚道德来评价的企业,极少。但它是一个终极目标,企业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奋斗。
(原载于 2009 年 5 月《新智囊》杂志)